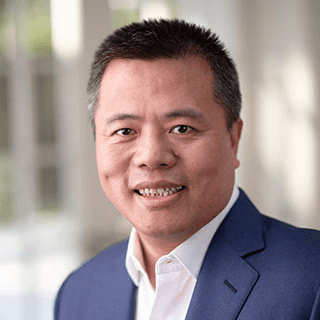言语道断,因果自现 —我心中的AGI是什么
言语道断,因果自现 —我心中的AGI是什么
• 03
过去这一两年,我们亲眼看着大模型的语言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跃迁:写作、总结、对话、问答、解题,越来越“像人”;HLE 之类的评测分数一再刷新纪录,连奥数级别的题目也能被系统性攻克。于是一个看上去顺理成章的结论开始流行:“所谓 AGI、大一统的通用智能,大概也就差不多了。”但在我看来,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
为了把这件事讲清楚,我借用一个比喻:今天主流的大模型,更像是“文科大模型”。它以语言生成与文本一致性为中心,把知识组织成“像真的叙述”和“像对的答案”。它的价值在于“模拟”:它能理解我们的委婉与修辞,能生成优雅的文字、逼真的对话、动人的故事;它会在教育、沟通、内容生产上变成新的基础设施,像电、像水,润物无声。但是即便它能解奥数、HLE 也能拿高分,这些胜利也大多发生在封闭系统里:题目定义明确、规则固定、对错可判、反馈即时。
但我一直坚信,人类真正需要 AI 去对抗的,是衰老、疾病、能源、材料、气候这些问题;这些战场不在考试题的封闭世界里,没有标准答案等你生成,只有现象、噪声、偏差、缺失变量与缓慢反馈;正确不是“写出来”的,而是被外部世界“确认出来”的。封闭世界的高分,证明了推理工程的成熟,但并不代表已经拥有了稳定的知识生产机制;高水平解题固然是走向发现的必要基础,却远非充分条件,因为真正决定未来的,不是封闭的叙述,而是那条冰冷而精确的因果红线;它关心的不是“说得对不对劲”,而是“这个假设能不能被现实否决或确认”;它的终极产物不是新作品,而是新知识——新的定理、新的材料、新的药物、新的工艺、新的工程结构。我把这种范式称为“理科大模型”。它的价值在于“发现”。
需要澄清一点:我说的“文科/理科”,不是两种模型的物种差异,而是两种默认动作的差异:文科大模型倾向给出一个“看起来不错的最终答案”,理科大模型倾向先给出一组可证伪的假设,并同时给出把这些假设变成证据的路径;文科模型在不确定处更容易把答案“凑圆”,理科模型在不确定处更像本能地停一下,然后去查证、去拆解,把问题拆成可验证的小问题;理科模型把因果当作第一公民,回答“条件改变后会发生什么”;理科模型还必须有可累积的长期记忆,把每一次验证得到的结论以可追溯的方式写回去。总之,理科模型更像一个握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:在无数方案里,识别哪一刀真正触及因果红线;它知道,一旦切下去,现实会给出最诚实、也最残酷的反馈,形成真正的因果闭环——这种对“真实代价”的敬畏,正是两种范式之间最本质的鸿沟。
所以,真正决定 AGI 应该是什么,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取向:我们究竟更在意一个能理解所有修辞,还能取代人类工作的“灵魂伴侣”,还是更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帮我们撕开迷雾、照亮未知,创造价值的“因果明镜”?我认为是后者。所以,实现 AGI 不是为了再造一个更会聊天的会生成的系统,而是为了打造一种“会发现”的智能。
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价值观去审视一下现有的 AGI 定义的主要流派。一种是行为主义范式,源于图灵测试,认为 AGI 的标准是“机器表现出的行为与人类无法区分”。这是目前大众最直观的评判标准。但如果一个 AI 只是在模仿人类说话,它永远无法告诉我们那些人类还没发现的真理。第二种是功能主义范式。以 OpenAI 为代表,定义 AGI 为“在大多数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中超越人类的自适应系统”,侧重于对人类劳动力的替代能力。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,都不是靠把旧工作做得更快,而是靠发现前所未有的新规律。第三种是能力分级范式。以 DeepMind 为代表,将 AGI 分为从 "Emerging" 到 "Superhuman" 的五个层级,核心指标是在广泛且未见过的任务中的“泛化能力”与“表现分值”。可现实世界不是考场,没有标准答案,真正的智慧是要在没有考卷的地方,自己找到那条正确的路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范式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问题。
那么我心目中 AGI 目标究竟要做什么?用一句话概括:它是一个 高可信、可验证、可纠错的通用推理引擎。在工程上能够做到三百步以上的复杂推理后,依然维持接近 99% 级别的整体正确率,并通过形式化和工具链把每一步推理“钉死”为可检查的证据,最终对任意复杂问题给出闭环解决方案。
为什么我们死磕“300 步”?我们必须先定义推理的最小单位——标准原子步(SIU, Standard Inference Unit),作为可审计的基本推理单元。每一步只执行单一逻辑操作,依赖最小必要输入,其结果可以通过工具或规则直接检验。按照这个标准,现在的大模型单步推理准确率最高能冲到 98%,哪怕每一步都能做到这个最高水平,300 步后的端对端成功率也只有 0.23%,已经接近归零。这意味着在 300 步之后,概率和运气基本失效,系统必须依赖可检验的推理与外部反馈闭环,而不是靠“看起来合理”的续写去蒙混过关。所以我认为 300 步是独立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“跨度起点”。
为什么 99% 必须是硬杠?因为发现式系统不是用来“聊天”,而是要进入现实成本区间:实验、工程、医疗、决策。低一个点的可靠性,就意味着高频的错误下注;而现实世界的错误,不是“答错题”,而是浪费实验窗口、烧掉工程预算、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耗。99% 不是面子指标,而是“可质押、可签字”的门槛。
所以,我心目中的 AGI,是能在 300 步的逻辑长征中,靠自我纠错熬过“概率死亡”,最终抵达地图之外的起点。 从这里开始,AGI 就可以在科学、工程、决策规划等任意领域里,作为一个可审计、可验证的通用问题求解器存在。
当然,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条“喊口号就能到达”的路线。把目标钉在“300 步仍保持 99% 可靠性”,本质上是在主动面对三个工程硬点:长链误差累积、开放世界验证缺口、以及组合爆炸下的预算约束。正因如此,我们在工程上必须进行解剖,将推理过程分为两层:逻辑生成层与检验层。生成层负责“想”:将大问题递归地拆解,直到细化为原子级操作,我们还要做检验层负责“查”:对每一个原子步通过工具、仿真或外部数据逐一验证。一旦某一步不过关,系统就在局部进行回退和重生成,而不是推翻整条推理链。
MiroMind 已经在这条路走出了第一步。 以 BrowseComp 为例,MiroMind 仅用 235B 参数模型就给出了 SOTA 的成绩,它的意义不在于“分数本身”,而在于证明了一个工程事实:我们正在把推理从“单次生成”推进到“时间序列上的反复求证”。更具体地说,我们不是依赖一次性长链思考去赌对答案,而是训练模型在更深、更频繁的 agent/环境交互中不断获取外部反馈并纠错,让推理过程逐步变成可审计的证据链。对我们而言,这就是“通用求解器”的第一块地基,然后在 99% 可靠性前提下逐步推到 300 步以上的跨度。这个过程沉默、缓慢、严谨、甚至有点残酷,它抛弃了人类语言的精妙模仿,却在枯燥、严苛、却能被现实反复复现的因果闭环中,缓慢破土而出,即使有耐心资本的加持和理想主义的坚守,这也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
佛经里有个词,叫“大圆镜智”。说的是一个人的心若能修到像一面大圆镜,就能如实照见万物因果,不被尘埃遮蔽,不被偏见扭曲,这是智慧的最高境界。我对这个智慧一直很向往,甚至创办的科普视频号也取名叫做大圆镜。而我心中的 AGI 就是一个无限接近“大圆镜智”的智能系统,不迷恋漂亮的语言,而是追问事实的真相是什么;不急着给出答案,而是去求证背后的因果是什么。在一个被语言和叙事塞满的 AI 时代,我们需要一面只对“因果和真相”负责的镜子。